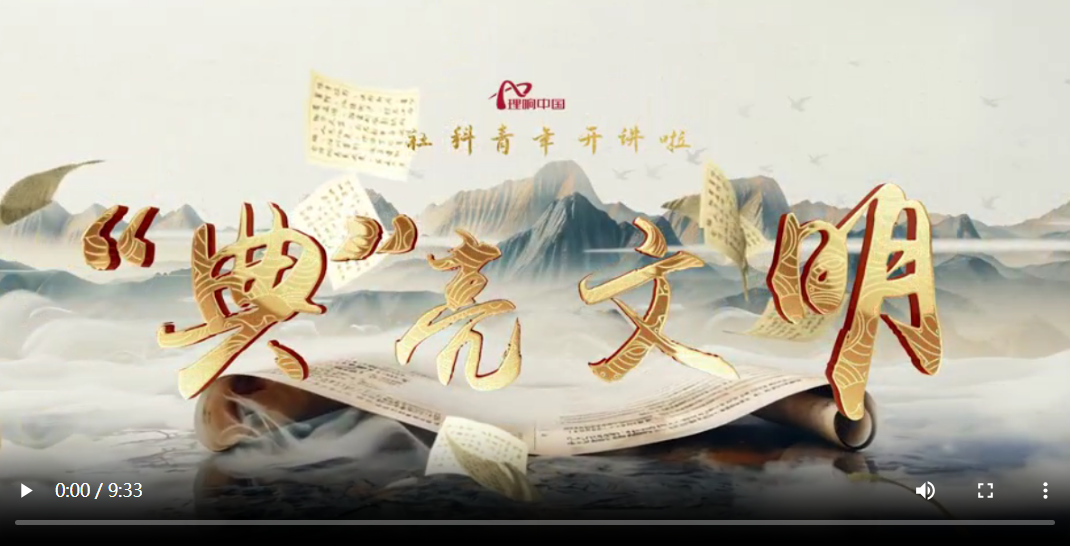【理響中國·社科青年開講啦@“典”亮文明】經典對當下有什么樣的傳承意義和價值?
當兩千多年前的中希文明,在亞歐大陸兩端點亮人類智慧的星火;當“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”的命題,叩響當下的時代之門。今天,我們循著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脈絡,與學者共探典籍里的千年回響。
主持人
唐萌,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文學編輯部編輯
嘉 賓
李芳,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
趙培,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編審
吳剛,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
唐萌:2024年11月,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開幕,值此一周年之際,我們又引發了關于古典、經典的一系列討論。下面,我想請三位老師分別談一談:何為古典?何為經典?經典對當下有什么樣的傳承意義和價值?
趙培:世界古典學大會,其實我們去看他們的發言題目,很多都是圍繞經典展開的。也就是說,前面兩個問題可以結合起來——什么是古典?其實我們通過對經典的了解,就可以回到所謂的古典時代。從“典”字形上來看,甲骨里邊就是說“典”中間上面是一個“冊”,下面是兩只手捧著這個東西,它是非常尊貴的。然后到了后來,比如儒家一般的經傳解釋里面,就把“經典”的“經”解釋為“常”,也就是說“經典”就是“常典”,什么是“常典”,它在我們以后的政治運作、社會運行,還有個人行為規范里面都能起到一個長久的指導意義。這個問題,其實原來有一個學術界都非常耳熟能詳的理論,就叫做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“軸心時代”理論,然后我們說,經典是軸心突破的成果,它既是軸心突破的成果,也是軸心突破的一個動力源。所以就出現了一個我們想要了解經典,先要了解“前經典”。“前經典”的時候,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是“前經典時代”人們處理的更多是“人”和“天”的關系。到了經典時代就是通過諸子(尤其是以孔子為代表的思想家),他們開始通過經典來處理人倫之間的關系,就是人和人、人和群體之間的關系。所以,從戰國諸子開始,經典開始脫離原來的狀態,或者說它開始慢慢地作為一個文本的經典開始獨立。獨立之后,我們所有的思考原點,都是圍繞這些典籍展開。春秋晚期到戰國的時候實現了一個經典的“完成”。
所以我們去看典籍的話,我們看到《莊子·天運》里面講,就是首次出現了“五經”排在一起的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春秋》。第二個點就是到了漢代,尤其是漢武帝以后,實現了我們說的“儒術獨尊”。“儒術獨尊”的時候,其實從經典的發展來講,就等于說經典從“完成”開始,它想進入到一個非常強的能夠指導我們現實生活,指導政治運作的這樣的一個(層面)。按照我們傳統的講法就是到了漢武帝以后,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”,就是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講法,這個時候經典就完全進入到了這套體系當中。并且后面經典的研習和傳承,一方面,它作為政治、社會、個人的準則,另一方面,經典本身的學習就變成了一個對經典文本的闡釋,也就是我們說的“傳”的進入,就經傳的進入。到了宋元以后,朱熹等宋代的學者,不滿足于漢唐的經傳系統,他們對它要進行一個重新的解釋。這個系統為什么要講?是因為它對宋元以后的中國社會影響非常大,尤其是元代它整個進入到了科舉考試之后,就是這一千多年來,士人學的全是這套體系,所以整個的經典總結下來,經典為什么重要?就現在我們為什么還要再重溫經典,還要再舉辦世界古典學大會,簡單說一句話,就是經典和社會文化一直是非常深度互動的,它塑造我們的傳統,然后我們的傳統也不斷地改變著經典的“經”還是“傳”的形態。所以它們一直是有一種非常強的互動關系,這種互動關系甚至到了現代,也持續在發生作用。
唐萌:吳剛老師是來自民族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,他從民族文學經典的角度,給我們談一談經典作為中華文化的經典以及民族文化的經典,它在中國以及世界上發揮的價值和意義。
吳剛: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當中,還有其他的講話當中提到了中國的經典,比如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、漢賦、唐詩、宋詞、明清小說。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到了“三大史詩”——比如藏族的《格薩爾》、蒙古族的《江格爾》、柯爾克孜族的《瑪納斯》。這“三大史詩”不僅屬于中國,也屬于世界。像《江格爾》在俄羅斯和蒙古國有流傳,像《瑪納斯》還在吉爾吉斯斯坦流傳,就是中國的“三大史詩”在國外傳播是比較廣泛的。另外一方面,中國的我們漢文化的經典典籍,它也傳播到了少數民族當中,比如說清代的時候漢文的典籍,像《三國演義》《西廂記》《金瓶梅》,通過滿文譯本傳播到了滿族、蒙古族等其他少數民族當中。這里邊比較典型的一個案例,比如《西廂記》,《西廂記》這個本子在清代康熙年間的時候,通過金圣嘆批改的《西廂記》傳播到了滿族當中,形成了滿漢合璧本;然后滿漢合璧本又進入到了蒙古族的傳統當中,形成了蒙古文的譯本。同時,它又進入到了達斡爾的文化傳統當中,形成了一種達斡爾的“烏欽”版本。它是個民間說唱,當時文人借用滿文字母拼寫達斡爾語,形成這樣一種手抄本,同時在民間傳唱。所以這就說明我們漢文化經典力量很強大,被我們中華各個民族所吸收接納。
唐萌:“他鄉有夫子,他鄉也必然有中華文化”。李芳老師可以給我們從俗文學的角度,介紹一下經典的傳承流變過程嗎?
李芳:趙培老師已經把經典的流變給我們梳理得非常清楚,但我想在我們討論這么充分的情況下,其實還是有兩個層面可以來展開我們對經典這個問題的探討。一個就是大家其實達成一個普遍的共識,我們今天來談古典學,是基于全人類的文明和典籍來討論的,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。至于我們做中國文學研究來談經典的話,我覺得一方面是我們怎樣在傳統經典里去梳理古典的這樣一種傳統。趙培老師的研究其實是順著這個脈絡來進行的。我覺得在當下重新建構古典學概念,需要去對其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。還有一個工作,就是我們在當下怎么重新去闡釋經典,所以我們可能在談經學研究的時候,覺得經學研究和經典它是一個先天可以等同起來的,雖然我們可能中間會有一些微小的差異,對吧?經典是不是又等同于經學,或者經學只是經典的一部分,或者經學當中的哪一個研究是經典的一部分,當然這個是趙老師他們研究的,可能對于我們稍微偏后一個時段或者研究俗文學的人,我們就希望在當下重新去闡釋經典,我們顯然不希望回到我們都很熟悉的古典文獻學,或者是這樣的一個范疇來討論,我們希望在一個更廣闊的空間來討論,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僅在談經學,可能在四部之外的集部典籍,也可以重新進入到我們的視野,以及它們在中國古代的這樣一個經典中的位置,我們可以重新討論。
從軸心時代鑄魂到多民族共賞,從經傳闡釋到世界流芳,經典始終是文化長河里不滅的光。